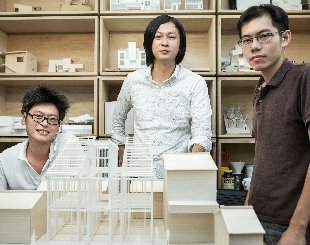這裡正是 Paul Engle 跟聶華苓在愛荷華的家,一個最開放、最自由的家,一個永遠有著聶華苓爽朗大笑聲的家。
 1967 年,Paul Engle 跟聶華苓在美國愛荷華創辦了「國際寫作計畫」(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,以下簡稱為 IWP),廣邀各國作家前來交流、寫作,當時許多生存在鐵幕之下的作家,都因為這寫作計畫,而有機會來到愛荷華一吸自由的空氣,「誰不能出去,我們就邀請誰。」聶華苓這樣說著,因此大陸的右派、台灣的左派作家,還有巴勒斯坦與猶太籍作家,竟也因此同坐在聶華苓的客廳中,雖然有時也會因為理念不合而大打出手,但是這裡自由的氣氛,反成了這許多作家生命中的一道出口,林懷民說:「他們不是在辦一個冷冰冰的學術計畫,這裡面完全是人的來往,所以我常說,在柏林圍牆被挖下來之前,那座牆,其實早就在愛荷華先被拆除了。」Paul Engle 跟聶華苓為 20 世紀文壇的努力用心,在 1976 年兩人同被推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。 (Photograph by 陳建仲)
1967 年,Paul Engle 跟聶華苓在美國愛荷華創辦了「國際寫作計畫」(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,以下簡稱為 IWP),廣邀各國作家前來交流、寫作,當時許多生存在鐵幕之下的作家,都因為這寫作計畫,而有機會來到愛荷華一吸自由的空氣,「誰不能出去,我們就邀請誰。」聶華苓這樣說著,因此大陸的右派、台灣的左派作家,還有巴勒斯坦與猶太籍作家,竟也因此同坐在聶華苓的客廳中,雖然有時也會因為理念不合而大打出手,但是這裡自由的氣氛,反成了這許多作家生命中的一道出口,林懷民說:「他們不是在辦一個冷冰冰的學術計畫,這裡面完全是人的來往,所以我常說,在柏林圍牆被挖下來之前,那座牆,其實早就在愛荷華先被拆除了。」Paul Engle 跟聶華苓為 20 世紀文壇的努力用心,在 1976 年兩人同被推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。 (Photograph by 陳建仲) 曾參加過 IWP 的作家們,都受過聶華苓如母親般的照顧,導演陳安琪透露,私下的聶華苓對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簡約的,但是對待這些作家卻總是那麼慷慨大方,不僅常邀請這些作家去吃大餐,更有些作家十分感謝地說,每每坐在聶華苓家中那張桌子前,你面前的碗與盤子絕對不會空著,這正是有著中國人好客包容性格的聶華苓讓大家備受感動之處,也因此那些去過愛荷華的作家們,總私下稱聶華苓為「華人文壇永遠的母親」。

聶華苓 (前排紅衣)與眾作家們合影。
聶華苓,是一個堅毅而溫暖的女性,而閱讀她的人生故事,就像是進行了一段 20 世紀中國歷史的壯遊。她的一生飄盪,1925 年出生在中國,因為父親是桂系人馬,一家始終在政治下惴惴難安;1949 年來到台灣,加入了雷震創辦的《自由中國》雜誌,擔任編輯一職,後因為白色恐怖《自由中國》遭停刊,聶華苓失去了工作,只好轉為在家埋首創作。1963 年,因緣際會遇到了畢生相知相惜的摯愛 Paul Engle,並隨他來到了美國愛荷華,展開了一段長達 27 年令人羨慕的愛戀繾綣,也自此開啟了 Paul Engle 與聶華苓影響 20 世紀文壇的志業——愛荷華的國際寫作計畫,讓文壇自此定要刻上他們一筆。
聶華苓生性樂觀,即便生活飄盪困頓,她總是以「嘿,就是嘛!」而一語帶過,即使對生活有怨,也不過是那剎那片刻;她性格豪爽,對待朋友後輩總像火一般溫暖人心,莫言曾這樣形容聶華苓:「她身上有種英雄氣概,甚至有一種俠義的情結。」因此這也是陳安琪想要拍攝聶華苓紀錄片的最主要原因,「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女性,非常值得我們去做一個借鏡,做人就應該跟她一樣,她的精神我覺得是很應該且值得傳給後代年輕人,所以這部影片也算是一部勵志片。」


聽著導演陳安琪爽朗的笑聲,讓人不禁聯想到電影中聶華苓接連不斷極富感染力的大笑。(Photograph by 李欣哲)
陳安琪與聶華苓的大女兒薇薇是初中同學,兩家往來密切,而在愛荷華時期,陳安琪也屬於 IWP 的一份子,鄭愁予、商禽當她是小妹妹照顧,中國作家教她一口啤酒、一口威士忌這樣喝酒,而到暑假,林懷民拉著她去看現代舞,而陳安琪則是帶著林懷民去打工、端盤子,陳安琪就像是聶華苓的第 3 個女兒一樣。
就是因為參與過愛荷華那段美好的日子,因此由陳安琪來拍攝聶華苓的紀錄片可說是再適合不過了,而在與導演訪談中,導演總是客氣的想要聽聽我們的想法,問著我們喜不喜歡這部作品,訪談間,當聊到愛荷華那段有趣的日子,導演也不時大笑出聲,而那迴盪的笑聲,彷彿也與影片中聶華苓的豪爽大笑重疊著。
Q:聽說一開始是計畫拍Paul Engle的紀錄片的?
A:其實拍 Paul Engle,就等於是拍 Paul Engle 和聶華苓,基本上他們是二為一體的,從 1964 年聶華苓去了美國,到 1991 年 Paul Engle 過世,他們幾乎都是在一起,因此 Paul Engle 的去世對她的打擊非常大,從 Paul Engle 過世 10 年左右,聶華苓幾乎什麼事都沒法做。
我在愛荷華的時候是跟他們一起生活的,當然也跟整個 IWP 是非常貼近;所以後來去加州念 UCLA,想要找一些 Project 來做,就想到可以拍 Paul Engle 的紀錄片,但回香港後就開始拍了一些廣告、劇情片,這個紀錄片的計畫就這樣一直擱置,後來在整理文件時,看到一封 Paul Engle 寫給我的信,是 Paul Engle 用舊打字機打出來的,很簡潔的兩句,「當然,我願意讓你拍。」看到這封信讓我很感慨,因為Paul Engle已經不在了;在愛荷華的那段時光,是多麼精彩的時代,也可以說是我的啟蒙時代,後來想一想,我還有聶華苓啊,馬上就打了電話給她,問她如果我要拍她的紀錄片,她就很爽朗地說:「好啊!」

導演陳安琪與聶華苓的感情相當好,因此由陳安琪來拍攝聶華苓紀錄片,可說再合適不過了。
Q:電影裡好像比較少談到聶華苓的文學創作?
A:這部份是我自己的選擇,第一因為我不是作家、學者,雖然我也喜歡看書,但我認為我沒有足夠的涵養去做一個更深入的探討呈現,所以在這部分我並沒有太過著墨;雖然我就沒有選擇從文學的角度去講聶華苓在文學上的成就,但很多看過的年輕朋友會說,這部片讓他們對看書的興趣又回來了,他們想要回去找聶華苓的書,還有影片中出現的這些作家的書籍來看,我想這也算是做到一種成果了。


Q:那導演如何去捕捉、去選擇素材來呈現聶華苓這個「人」?
A:慢慢的、慢慢的拍,所以這部片花了很長的時間拍攝,我覺得最不容易的就是這個。我並不打算拍一部文學電影,我希望呈現出聶華苓的人生、故事與波折,就如同她自己說的,她的一生就像動盪的中國 20 世紀,抗戰、國共鬥爭、大陸赤化、台灣白色恐怖、解嚴,到台灣邁向民主社會,這些都是歷史上重要事實與事件,歷史的演進最終希望人類都可以擁有自由,這也是聶華苓跟 Paul Engle 推廣 IWP 最主要、最重要的主軸,為人最重要的,就是擁有自由跟尊嚴,尤其如果你是生長在一個沒有自由的地方,就特別覺得自由的珍貴了。
IWP 背後一個很重要的想法,就是要讓這些失去自由、身處在水深火熱環境裡的作家,有機會離開國家,來到愛荷華的這一年裡,他們可以很自由地從外面的世界去看自己國家內部的情況,之後很多作家都還是選擇回國,以地下的方式爭取國家人民的自由;因此聶華苓跟 Paul Engle 的影響是很深遠的,不僅只在文學上,後來他們兩個也都被提名和平獎。
Q:影片最後有段讓人印象特別深刻,就是提到聶華苓拿出那件銀色的衣服說要當她的壽服,我覺得這段特別能夠呈現出聶華苓灑脫的大氣。
 A:很多人在那段都落淚,那部分可以很真實地看到聶華苓的性格,即使是面對自己的死亡,都沒有恐懼,就是這樣子了,就像她書中所說:「我就像那條河,慢慢地流,慢了,慢了,有一天我就走了。」無愧、無怨地離開了。
A:很多人在那段都落淚,那部分可以很真實地看到聶華苓的性格,即使是面對自己的死亡,都沒有恐懼,就是這樣子了,就像她書中所說:「我就像那條河,慢慢地流,慢了,慢了,有一天我就走了。」無愧、無怨地離開了。Q:為什麼在片中導演想要呈現聶華苓去購物,還有一位先生到聶華苓家中收取維修費用的片段呢?
A:為什麼不呢?那就是人生活最精采的地方啊,如果沒有那些片段,我相信這片子就絕對是會很悶。因為每個人都是立體的,生活的片段才能呈現更完整的聶華苓,而這些小細節可以讓聶華苓變得更加深刻,這些小地方是我最喜歡的。
Q:尤其影片中提到聶華苓的大笑,然後導演就剪了好多好多聶華苓的笑聲,那個笑聲很像有感染力,讓大家都跟著大笑。
 A:我朋友也說那一段很精彩,有一個大陸的第一代導演在大理看這部片子,看完後就跟我說:「陳安琪,妳應該在那個哈哈哈哈大笑那邊就停了,然後就成就了這位傲笑江湖的俠女。」其實這種呈現方式也很有意思,不是不可以,但只是我們的選擇是讓整部片子淡淡、慢慢的,沒有什麼很煽情的。
A:我朋友也說那一段很精彩,有一個大陸的第一代導演在大理看這部片子,看完後就跟我說:「陳安琪,妳應該在那個哈哈哈哈大笑那邊就停了,然後就成就了這位傲笑江湖的俠女。」其實這種呈現方式也很有意思,不是不可以,但只是我們的選擇是讓整部片子淡淡、慢慢的,沒有什麼很煽情的。Q:為什麼導演會選擇林懷民、蔣勳等作家來談聶華苓呢?
A:因為我們覺得蔣勳那兩段講得真的很好,而林懷民的柏林圍牆比喻也講得很好,我自己有點遺憾的部分是,我們大概訪問了 30 位作家,但有的作家可能在影片中一個鏡頭都沒有,或有的作家只有一個鏡頭,其實這些作家很多都是講得很好的,但是因為有些講得有重複,如果收錄太多講述聶華苓的訪談,對這影片的節奏也有影響,因此只好忍痛割捨。
現在很多年輕人根本不認識聶華苓,雖然她的著作不多,但是她的文筆真的很不錯,就像她弟弟說的,那些短篇真是精采地不得了,當時聶華苓剛到台灣,看見周圍的小市民的那些小故事,真的好棒。後來因為國際寫作計畫,太多事情要做了,犧牲了她寫作的時間,但是那成就是更大的了。其實這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,並沒有太多人知道,這真的很奇怪,可能是因為聶華苓比較低調,加上文學在社會上也屬於比較小眾的領域,但是文字是連繫歷史,聯繫你我的,我們怎麼可以把文字丟棄呢?

聶華苓的人緣相當好,有太多作家曾在愛荷華受到其照顧,因此非常願意在紀錄片中露臉向大家聊聊他們所認識的聶華苓。此為作家莫言所簽下的「同意擔當顧問併接受採訪書」。
Q:請導演多分享一些與聶華苓、Paul Engle 生活的片段,或是與這些作家們相處的有趣故事。
A:打架、吵架都是曾經在那邊上演過,有時候真的就是一個杯子這樣飛過去,影片中提到的埃及跟以色列作家,之前還有巴勒斯坦與猶太籍的作家,他們一見面就真的先打起來,相較來說,華人作家在這方面就比較有禮貌,即使理念相當不一樣,但是見面的時候還是很客氣的,雖然在討論的時候會吵,但是拿這些議題來開玩笑也是不少。
另外,還有一個作家煙癮非常大,有一次抽菸忘了開窗,結果竟引發煙霧器,嗶地讓整個宿舍都浸泡在水灘中,真的很多這種小故事。而我最記得的就是中國作家教我們喝酒,還有一次林懷民跟我說:「安琪,我帶妳去紐約。」結果,他帶我去看了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的現代舞表演。
那個年代真的是很快樂的年代,大家一起經歷嬉皮、婦運、反越戰,那時候在美國受到的薰陶,讓我學習怎麼培養自己的看法,而且也因為 Paul Engle 跟聶華苓的看法跟我的也很相近,所以講這個故事就顯得容易多了。
Q:那聶華苓看過紀錄片了嗎?她有什麼想法?
A:影片完成剪接後,我最怕的就是她那一關,很怕她不喜歡、不同意,尤其聶華苓是很要求完美的;所以我拖到最後,才寄給她看,然後開始膽顫心驚地等待,結果有一天mail來了,很簡單的幾句,她說她看了,非常非常地 touch。那是拍這部片以來,我最開心的片刻,什麼都值得了,我真的很開心有這個緣分可以完成這件事。
Q:可以請導演談談現在的香港電影產業嗎?
 A:聶華苓曾經讚美一個作家:「他有寫作的功夫,也有背後精神的深度,那就是好作品。」我覺得電影也是這樣,內容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,現在我看電影,都會期待能不能在最後帶走些什麼,希望電影有多一點想說的東西,有一點思考,這才是我珍惜的電影。
A:聶華苓曾經讚美一個作家:「他有寫作的功夫,也有背後精神的深度,那就是好作品。」我覺得電影也是這樣,內容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,現在我看電影,都會期待能不能在最後帶走些什麼,希望電影有多一點想說的東西,有一點思考,這才是我珍惜的電影。現在香港電影技術面上是很好的,但在電影製作的制度上還是沒有進步,為什麼好萊塢電影拍起來沒有那麼辛苦,因為大家都分工合作得很好,制度很成熟,香港的拍片方式像是打游擊,很辛苦,但如果大家都累得半死,如何去做好一件事情呢?
所以說如果要我回去拍劇情片、商業片,我真的捱不下去,我現在被稱為邊緣外的導演,因為路不一樣了,但我覺得這樣很好啊,做自己喜歡的,滿足感很好,也覺得無愧!
採訪整理/劉宏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