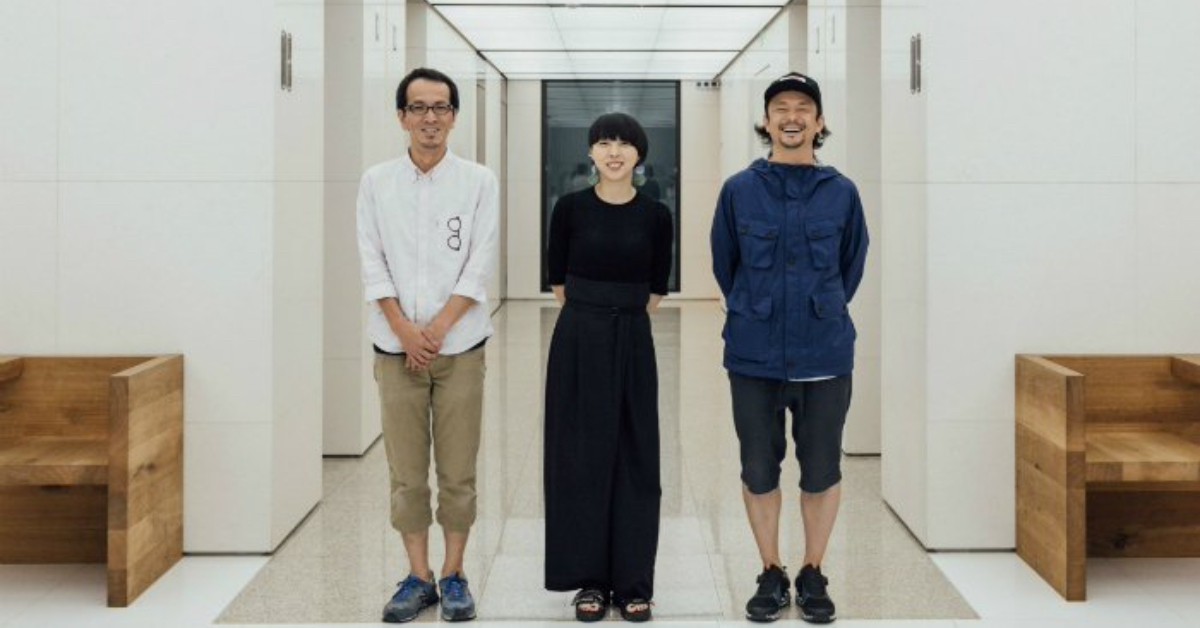近四個小時長的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在「山屋」中不斷重播,導演楊德昌透過幾個簡單的場景、單純的故事線,卻細密抽絲 1960 年代不同年齡層纏綿又複雜的人際關係。「我喜歡它簡單而豐富的現代性」邱文傑說,如果這部作品說出台灣電影的現代性,那台灣建築的當代性,又可以如何表達?
這些年,建築人不斷尋找的台灣自明性
每當漫步街頭,發現老屋的鐵窗、細密的磁磚與雕花玻璃,或走訪某座 60、70 年代粗獷主義建築時,也許就讓人心生「真是台灣啊!」的感覺,但若說起什麼是真正能代表當代台灣的建築,我們心中似乎又打上了一個問號。
台灣其實一直在探索屬於本土的建築形式。邱文傑建築師也在這幾十年,不斷擷取台灣日常元素嘗試,對於台灣當代建築,他觀察尋找文化自明性的建築師不多,仍持續著墨這件事的,大概就是黃聲遠建築師,「他的建築像寫實的水彩,用比較浪漫活潑輕鬆的樣態去談台灣的鄉土。」邱文傑說。
「不過聲遠的形式比較『魔幻寫實』,我認為我是比較『抽象』」邱文傑說,「山屋」的表達手法,邱文傑堅持現代建築教育的「Discipline(自律性)」,重複咀嚼台灣「巷弄文化」人與人的關係,希望不媚俗地,不向政治正確靠攏地,訴說另一種台灣建築的可能。

「山屋」以鋼筋水泥為基座,一樓以台灣日常「騎樓」生活為概念,轉化為建築前巷與後街互通的設計;上方輕盈的「輕鋼構」則像是將邱文傑記憶裡的違章,揉合現代建築理性思維重新演繹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
建築師邱文傑說,這座建築其實就是「想像台北的天空出現一座宇宙戰艦,在一秒鐘內把所有鐵皮屋吸光,丟到熔化爐裡,生產出 9x9 公分的方管與 6t 厚的鋼板,煉成這座『山屋』!」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用建築的語彙,串起在童年「騎樓」玩樂生活的記憶
走進山屋一樓有種親切感,因為這裡就像是處處可見的「騎樓」,也是邱文傑小時候住在林森北路條通,難以割捨的童年場景。
過去林森北路一代大部分都是國民黨官員後代、醫生、律師的住所,1979 年北投廢娼後,聲色場所遷移到此,才逐漸改變社區的氛圍。在這之前,住家附近的騎樓就是鄰里孩子們的遊樂場,捉迷藏、鬼抓人......什麼都可以玩。比如說打棒球的遊戲,大夥們把條通騎樓的兩根柱子當作本壘、一壘,越過中山北路對面的兩棵樹是二、三壘,「兩根柱子兩根樹圍成一個菱形,對準對角線打,打到中山北路上就是二壘安打,一打到中山北路對面就全壘打!現在回來想都覺得好好笑,那時候全壘打很簡單,跑步穿過大馬路就把球撿回來,好像都沒有車一樣!」邱文傑笑說。

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而且騎樓似乎有種魔力,不論是遮雨、玩耍、做生意,各種生活的可能每天都在「騎樓」展開。也許騎樓賣冰的店家為了增加收入,將前方的柱子租給賣彩券的阿嬤,微小的柱子又養活了一家人,「多少人在這裡生活、擦身而過,那個狀態對我來說很迷人」邱文傑說。因此,他把記憶裡的場景搬進「山屋」一樓,變成讓附近的街坊鄰居可以穿越、來往小巷與公園的「騎樓」,像城市的捷徑,更是個人與人交會的場所。

一樓 RC 結構在邊界刻意突出懸板,讓人更有走在騎樓下的感覺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
邱文傑建築展《間·接·共·生》展出白先勇《台北人》〈永遠的尹雪豔〉篇章,書中所提及中山北路上的「玫瑰鮮花店」,正是由建築師的父親所經營,過去許多國民黨達官顯貴交關捧場。《台北人》所訴說的生活氛圍,不同於巷弄文化充滿有機感,但也是他成長記憶的一部分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從台灣的「亂」萃取養分,再解構、幻化成輕盈的鋼構
「有人說鄉愁沒什麼,但也有人說,到老回望一切,功成名就也好、淒慘潦倒也罷,其實鄉愁和你的第一個情人一樣,是會記得一輩子的事。這樣來說,我好像找到了什麼,不是再那樣漂泊了。」邱文傑說。
順著樓梯往上走,二樓以上是構築在水泥基座上的輕鋼構。違章建築那股不必刻意就兀自散發的有機感,似乎讓邱文傑從年輕到現在都心心念念的。他選擇一般人設計輕鋼構時不會想到的「滿焊」工法,拜託師傅焊接所有構建、結構。一道道焊痕,加上具避震功能的交叉「斜撐」結構,都有違章建築恣意在都市裡生長、生猛粗獷的味道。






以「滿焊」工法連接鋼構,不加以修飾,呈現出建築材料的本質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

建築使用許多圓棒、斜撐結構,在建築上構築粗獷的張力,同時具有對抗水平地震力的效果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但「山屋」想說的,不只是城市由下而上的生命力,還有直到現在我們自己都還在用力釐清的身世。「我當然知道『混雜在一起』有時候很美好,夜市就是個例子,那是生命力的展現,但不是什麼都應該這樣。」邱文傑接著說,台灣戰後地景受到政治氛圍影響,大家總覺得最終還是會回到大陸,政府也就默許這些簡易、臨時的建築蔓延都市,「如果真是臨時也就罷了,它卻變作我們的永久。某種層次我也希望有像中國五千年的文化讓我來玩,但我們沒有,即使是閩南文化也與中國相差不遠。我長大的地方就在這裡,相較下這麼淺層的五、六十年,最有感情的就是那些條通、臨時性建築,所以我不得不在這樣的環境裡去萃取養分。」

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鐵皮也好、違章也好,那股親切感對建築師來說,是回憶,也是根,可是台灣如果繼續停留在鄉愁的表層,便走不到國際建築的當代性。所以邱文傑很抽象、浪漫的想像,把城市中違建常用的鐵皮、C型鋼、圓棒......全搜集起來「燒掉」,幻化成輕鋼構。如此既有台灣市井的輕與亂,同時又恢復向來被違章所佔據的公共空間,把屋頂平台原本的開放性還給城市。
將回憶與鄉愁裡人與人的關係,轉化為「AxB 間接共生空間」
而更往裡面探入,你會發現「山屋」的內在與粗獷的外表形成對比。這份「鄉愁」從外在「輕」與「亂」的形式,走向巷弄文化人與人之間最緊密的關係。
二、三樓空間中央像個被紗網包圍的盒子,裡、外的人可以隱約看見、聽到彼此,卻無法穿過這個空間,細膩的表達「AxB」兩個異質性空間交纏而不相融合,人與人之間緊密卻更為彼此思量、帶有舒適感的「間接共生」狀態。(什麼是AxB?延伸閱讀:邱文傑建築展《間·接·共·生》開展!走入「山屋」,反思如何讓台灣巷弄文化回應至下一代建築!)




白色的紗網分隔了「山屋」二樓右邊的「A」空間與左邊的「B」空間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
「山屋」二樓紗網內的「B」空間,《間·接·共·生》展覽期間投影台灣的街道騎樓影像,在「A」空間看展時,也能隱約看見這裡的光影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
「山屋」三樓播放電影《估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、放置書籍《家變》、《台北人》,說著台灣上個年代的故事。走到底端,可以通往望向二樓「A」區的平台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這個想法其實來自小時候玩的一個遊戲「Catch me if you can」,糾結的遊戲樣態是對峙關係的典型範例。「那個遊戲在我們那幾年就失傳了,連我都忘了,大概十年前,小時候的記憶突然回來,就印在腦海裡揮之不去。」邱文傑說。這也像他在紐約唸書時,看到普立茲克獎建築師 James Stirling 設計「斯圖加特國立美術館」的概念。James Stirling 透過橫穿過美術館、進到中庭的公共步道,讓參觀的人、城市裡交通的人相會,公共空間侵入過去象徵威權的美術館,這種異質性空間交錯、人們來往的動態感,甚至是透過建築手段打破權威性,都深深吸引著邱文傑。


從一樓通往到頂樓露台的旋轉樓梯,是「B」空間的獨立出入通道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

除了A、B兩個獨立出入口,二樓到四樓也設計了樓梯,樓梯四樓以上空間則以玻璃延伸至屋頂,具有「煙囪效應」導熱效果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「但『山屋』空間交纏的狀況,我覺得大家還在消化,我也在測試到底值不值得這樣做,因其實還沒有真的做出來。」邱文傑說。山屋做了許多不同以往的嘗試,但目前還沒有真的兩個異質功能進駐,空間的可能性也尚未被完全彰顯出來。
不過在確保空間的公共性、私密性的前提下,「AxB」能感知到彼此的空間,其實就像將原本台灣巷弄內各種功能空間彼此混亂、有機交融的狀態,用建築的手法加以分隔,又不失去那股親密感,讓人隨時可以感覺到城市不斷運轉的脈動。
「想像如果一座圖書館中間有個 shopping mall,介面全部是不會有聲音干擾彼此的雙層玻璃。在圖書館讀累了,建築做一個小陽台能看到在 shopping mall 購物的人,偶爾就能開個門透氣,像現在『山屋』三樓就有個平台可以走出去,能看見二樓的人在看展覽。」邱文傑說,AxB 空間可以多麼不同、介面能夠如何營造靠近與疏離感,是他未來仍會再繼續探索的方向。
不過在確保空間的公共性、私密性的前提下,「AxB」能感知到彼此的空間,其實就像將原本台灣巷弄內各種功能空間彼此混亂、有機交融的狀態,用建築的手法加以分隔,又不失去那股親密感,讓人隨時可以感覺到城市不斷運轉的脈動。
「想像如果一座圖書館中間有個 shopping mall,介面全部是不會有聲音干擾彼此的雙層玻璃。在圖書館讀累了,建築做一個小陽台能看到在 shopping mall 購物的人,偶爾就能開個門透氣,像現在『山屋』三樓就有個平台可以走出去,能看見二樓的人在看展覽。」邱文傑說,AxB 空間可以多麼不同、介面能夠如何營造靠近與疏離感,是他未來仍會再繼續探索的方向。

三樓紗網內的空間向外延伸出一個平台,可以望向二樓「A」空間正在看展的人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「自律」與「自由」的拉扯,如何透過當代建築呼應台灣巷弄文化
也許因為我們迂迴的歷史,到了21世紀我們還在問「所謂的台灣性到底是什麼」?龔書章老師曾用 Italo Calvino《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》中談論「輕」的價值,來比喻邱文傑面對心中「台灣建築」的態度。Italo Calvino 引述了一段希臘神話:柏修斯為了不正視鮮豔欲滴的女妖梅杜莎,而運用盾牌的反射,揮刀砍下梅杜莎頭顱。
在許多自認具有「台灣性」的建築都已走向媚俗化,似乎要夠亂、夠有機才叫做台灣。龔老師說,邱文傑像是拿著盾牌在面對內心那塊最豐富的巷弄文化,「他其實是想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去建構材料、結構,但他又對於實際生活的事物很迷戀。可是他跟別人不一樣,他常說『我們不能太濫情,我們必須能不要那麼政治正確』,其實邱文傑的建築一直在抵抗政治正確,抵抗那些很豐富的、雜亂的、沒有次序的東西。」(註1)

建築水泥基座四個角分別設計了「方井」,作為雨水回收系統最後通向植栽的管道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
建築水泥基座四個角分別設計了「方井」,作為雨水回收系統最後通向植栽的管道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
在騎樓空間,混凝土、管線皆直接裸露在外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或許是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教育影響,邱文傑說「我其實是容易很ㄍㄧㄥ的人,隨便畫一條曲線不太敢畫,我的『Discipline(自律性)』會馬上出來。就像 921 地震博物館,如果沒斷層我根本畫不出曲線!」比方,從「山屋」建築管線設計全部都做明管,加上室內水電管線也裸露在外,幾乎不做天花版裝飾遮掩,就能看見邱文傑老師所說的「自律性」(雖然邱建築師笑說他還是在二樓冷氣複雜的管線偷偷「作弊」做了天花收納,但大部分都是很直接的不以裝飾遮掩)。
用當代建築的角度思考,他覺得所有的構造必須有功能,而不是像後現代主義浮華的裝飾聲稱自己的台灣色彩。「台灣如果要談建築,無論多鄉土,最後詮釋的方式我希望是比較『自律的』,因為台灣其實已經夠亂了,要跟世界對話,最重要的是 discipline 的語言。」邱文傑說。


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不過最有趣的是,在這麼嚴謹自律的「山屋」裡,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二樓玻璃窗旁如隨風飄起的皮層,那種有點不照規矩的 DNA,或是到了施工現場「覺得不過癮、為什麼一直那麼嚴肅」而掀起的二樓玻璃窗。或許暗自的呼應了龔老師說「我覺得他的『輕』不只是外顯的輕,還是一種『自由感』。他總是不小心會把感情露出來,這也是他的掙扎和他最可貴的部分,因為其他的建築師不見得這麼自覺。」(註2)




從四樓空間望出去,周遭住家都是鐵皮加蓋,衝擊感相當強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

右圖二樓刻意設計了飄起的皮層,這扇窗戶也是施工期間,建築師跟隨當下內心的想法而掀開的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、彭永翔)


從四樓空間望出去,周遭住家都是鐵皮加蓋,衝擊感相當強。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無論如何,邱文傑建築師還在往前走。「現代建築」是手上的工具,形式以外,他更想透過建築傳達「好的關係」,也為此成立了「AxB Architecture Studio」。蓋了將近十年的山屋,邱文傑特別感謝業主杜書拯先生,一直支持著他實踐內心的想法。一路以來邱文傑很堅持,但初衷卻再單純不過,「如果有一天回望這一切,能發現台灣有一個人,竟然把日常生活的巷弄文化做成了現代性的東西,而有別於以中國文化為標準,想突破些什麼,其實就夠了。」他說。

(Photo Credit:MOT TIMES、Photography by 余松翰)
註1、2:引述自《間接共生》論壇「再新銳-建築曲折路」
編輯/林沛伶